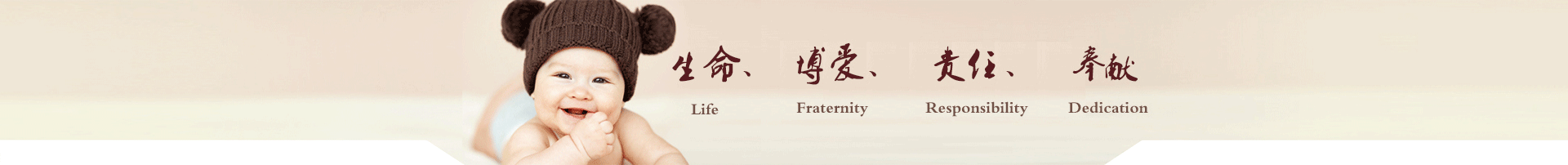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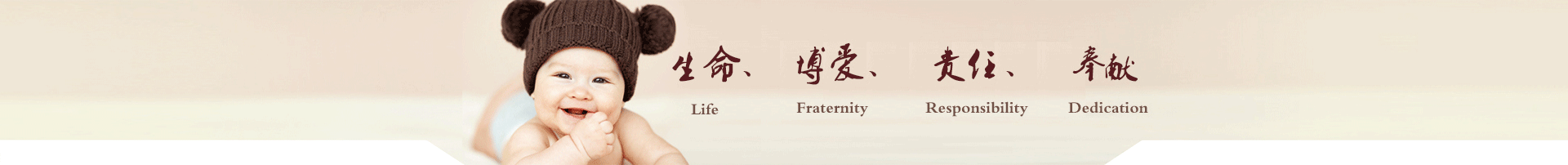
文|太阳日记
1
我的老家在鄂西北秦巴山区的一个叫“关沟”的村子,这里巍峨的高山层层叠叠,距离县城一百多里、本镇五十里,我的父亲母亲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。我每次回家,需要坐了火车又转两趟汽车,再步行二里山路才到。
自从我小侄子龙龙和小侄女妞妞搁在家里后,除了父亲母亲,我的心头又多了一份牵挂,时不时地想着回。又半年不见,龙龙和妞妞已经不认识我。他们特别怯生。黄昏,我走到家门口的那一刻,见了我,一个害怕得赶紧躲向我母亲的身后,一个“哇”地一声哭着朝我母亲的怀里钻。
我一愣怔,笑了笑。哭的是妞妞。我母亲说:“是你姑,怕啥呀?去看姑姑回来买好吃的没。”妞妞好像来了兴致,马上转脸,怯怯地瞄瞄我,把头重新扎下去。龙龙在我母亲的身后听了,也好奇地探出头来打量我。
进屋后,我放下包,去翻父亲给我拿回的行李袋。两个行李袋,里面装满衣服和吃的东西,有点重,父亲在沟口的车路上接到我,用扁担挑回来。在我还没在行李袋里找出什么时,两个小家伙跟在我母亲的身后进来,站着远远地观望。我又一翻找,翻出两个蛋糕,哄他们快到我的身边。龙龙看看蛋糕,兴奋地朝前跑几步,伸伸手,又后退回去,木着脸,一动不动。妞妞则一边伸着小舌头,一边眨巴着眼睛,两只小手在胸前搓来搓去,始终没有上前。我便主动靠近他们。他们直躲,弄得我追了两圈,他们才接到手中,立刻去找他们的奶奶。
龙龙和妞妞同样穿着紫褂。衣服又粗又长,有点脏,我母亲说这是护衣,小娃子穿衣裳脏得快,套一件这种护衣,里面的衣服就耐脏一些。但是,我觉得这护衣也太土气了,他们穿在身上太臃肿,包到了屁股,像个小老人。我还发现,龙龙和妞妞的说话发音清晰了很多,一下子都会表达自己的意思,龙龙能够自己跑得快,妞妞比她的哥哥个头高一点,都偏瘦。看着他们全围在我母亲面前嚷着要吃,要奶奶剥了包装皮,我一阵心酸,跑到堂屋门前,朝对面的山峰望去。山就像一头巨象,高高地堵在那里。山中的一大片树林,在秋日的晚霞中,青着眼,红着脸,像醉鬼,包围着星星点点的几块庄稼地。蜿蜒的山路上,没有一个人。我想,我的父亲母亲和侄子龙龙、侄女妞妞,生活在这个地方,不仅日子过得不容易,而且完全孤独。

龙龙和妞妞在深圳出生,龙凤胎,一岁零两个月带回来。把他们搁在家里,纯粹是无奈之举。起初回到家里,他们哭闹不止,不是争抢着要我母亲一人抱,就是要找爸爸妈妈。我母亲没有办法,着急了,就用手拍一下他们的屁股。一拍哭,只得继续哄。
龙龙和妞妞的眼睛都大,在这方面继承我哥哥和嫂子。倒是又听我的长辈们说,龙龙长得太像我哥哥小时候,妞妞长得太像我小时候。妞妞的脸蛋小小巧巧的,嘴巴翘翘的;她哥哥胖一点点、眉稍浓。我并且观察到,龙龙对于一个事物的耐心多一些,而妞妞很敏感。
我这次回来,在家里和他们玩熟后,教他们认字,带他们绕着村子转一转,又发现他们俩特别爱说话。他们还爱看虫子、看蚂蚁、看猪、看狗、看月亮、看云彩、看南瓜、丝瓜这瓜那瓜。
若谁问你爸爸妈妈呢?他们会回答,在深圳。想不想他们?想,一个说。不想,另一个说。想与不想,他们回答的很随意。虽然时常通电话,爸爸妈妈,在他们的眼里恐怕很模糊,具体是什么意思有可能也弄不清楚。一年多不见,他们已经忘记他们了。
2
在家里,我父亲和母亲是分工的。我母亲负责照看龙龙和妞妞,我父亲负责地里的活路。
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。他每天早上天不亮便起床。除了下雨上不成坡,其他日子在天麻麻亮就下地干活。有时候,我母亲给龙龙和妞妞穿了衣服刚起来,正在吃早饭,他干了半晌活恰好回来。他进屋抱住酒瓶咂两口,扒一碗饭,吃一根烟,又要上坡。他不是去黄连垭敲芝麻,就是去对门凉挖黄姜地、沟滩挖花生、土包打草药……村里的山上,被我父亲踏个遍。他顶着一头白发,在山上弯腰弓脊地干,顾不上纠缠自己多年的高血压和气管炎。有孙子孙女,就不敢倒下。
有时,我父亲要上坡,背着挖镢刚走出屋门,妞妞就从后面追来,叽咕着要跟爷爷一块儿去。山路又滑又陡,领着她不方便,我父亲急着走,不能领。妞妞一直把他追到院头,他笑着劝,劝不动,就转过来抱一下她,再交给我母亲。逢他从地里回来,妞妞和她哥哥又争着叫爷爷,像小狗一样朝他的跟 前围。一声爷爷叫的,我父亲好像再累也不累了,连忙答应。他喘着气坐下来,用一双木柴般粗糙的大手拤住妞妞的腰,把她一把揽在怀里。妞妞高兴得咯咯笑个不停。我父亲也笑起来,逗着她:“看我家的妞妞好乖!”这样的时刻,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温馨。骨肉分离的烦恼、守着大山的孤寂,似乎暂时全被取代。
前围。一声爷爷叫的,我父亲好像再累也不累了,连忙答应。他喘着气坐下来,用一双木柴般粗糙的大手拤住妞妞的腰,把她一把揽在怀里。妞妞高兴得咯咯笑个不停。我父亲也笑起来,逗着她:“看我家的妞妞好乖!”这样的时刻,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温馨。骨肉分离的烦恼、守着大山的孤寂,似乎暂时全被取代。
我父亲还怕孙子孙女摔跤,就在院边栽上树桩,又砍了竹子围起来。龙龙和妞妞,乐意在院子里一圈圈的赛跑。每每,我父亲见了,好像是见了他莳弄的庄稼苗在长高,脸上流露出某种舒坦。在他的眼里,他得首先把庄稼弄好,闲暇时,可以陪陪龙龙和妞妞。
庄稼,是他肩上的担子。种了大半辈子地,他怕不种没吃的;不种,地越来越荒。我们家的地已经荒了几块,还有几块给别人了,剩下的几块地不能丢失。他要种,用自己最大的能力种。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,气管炎一时一时地犯,有时,吃一口烟或喝一口酒也咳嗽起来;头时常昏昏沉沉的,担东西得慢悠悠地走;手,倒开水、盛饭也发抖。即便这样,他必须支撑自己。
为了趁早干活,我父亲大多早上不吃饭上坡。他穿着土布旧衣,戴着草帽,夹把镰刀、挖镢或一只布袋,穿过树林,到山上干一会儿活,太阳才爬出来。他种黄姜、芝麻、花生、苞谷、绿豆、黄豆、油菜,不让地闲着。苞谷穗长得大,他便万分喜悦;黄姜的价格偏低,他有点惆怅。在我体会到我父亲如此辛苦时,我感到惭愧。也许,我最大的愿望是让他和我母亲安度晚年,可我没有做到。
听我母亲说有一次我父亲在别处喝醉酒了,在山路上摔了一跤。天快黑了,龙龙和妞妞等不到爷爷回来,就站在院边你一声我一声地喊。喊了好久,待他回来,只见整个人的头上鲜血直流。我听了后,感到害怕。从母亲的口中和脸上,我更感觉到她当时的惊慌。
3
我母亲只比我父亲小一岁。她的头发,比我父亲还白得多。关于白发,我记得在我年少时,我母亲就有。那时只有几根几根的,现在满头长,像戴着棉花帽,白得可怕。她的皱纹也多,像犁沟,从黄土似的干燥、松弛的皮肤上犁出一条条小沟子来。给我的感觉是,我母亲真的老了,比实际年龄老。
看孩子,这个活,并不比种庄稼轻松。 我母亲老了老了还要看孩子。我看出,她很累。
我母亲老了老了还要看孩子。我看出,她很累。
我母亲每天早上起床后,就去厨房。等她做好饭,龙龙和妞妞才醒。她听到哭声,从厨房大步跑到床前。通常妞妞先醒。她已经蹬开被子坐起来,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,两疙瘩泪水挂在脸上。一看到奶奶,妞妞破涕为笑。龙龙也被妹妹聒醒,睡在被窝里,像吹喇叭似的哭叫不止。奶奶来了,龙龙嚷着要起,我母亲担心妞妞着凉,得先给她穿。龙龙在一边还在哭。在他的哭声里,我母亲给妞妞穿衣的动作得麻利点。实际上,她一个上了岁数的人,一双皱巴巴的手免不了笨拙。越是急着穿,越是穿得慢。穿了马夹,穿外套,穿护衣,掂她尿一脬尿,再穿裤子、袜子、鞋,按顺序来。总算穿好一个,我母亲给龙龙穿,妞妞在一旁嚷着要吃东西。我母亲哄着等哥哥起来,洗了脸一块儿吃,妞妞不同意。不给她拿点吃的东西在手中,她就哭给你看。
若是碰到龙龙醒来不哭,或妞妞穿好了衣裳不闹,我母亲好像轻松了半截。两个娃娃全部穿好,去洗脸、洗手,然后盛饭。他们每人端着一只小碗坐在桌前,自己吃几嘴,还得我母亲一一喂。喂好龙龙和妞妞,饭也半凉子了,我母亲匆匆吃碗把。然后,在我母亲洗碗时,龙龙和妞妞一个趴她的屁股上,一个抱着她的腿,纠缠着去大路上玩。
大路上也没什么好看的。路边是庄稼,路上是野草和石头,一次次地走,都是这些,但龙龙和妞妞天天想来。我母亲关上门,抱一个,拉一个上了路。他们在路上走走停停。常常妞妞走一会儿,发了懒,让抱。我母亲瘦瘦小小的个子,一次抱不动两个娃,只好哄着龙龙从怀里下来,抱妹妹。龙龙同意了,他下怀走一会儿,又让奶奶抱。我母亲只好再哄妞妞自己走,抱哥哥。这样轮换着抱,晃一圈回家,我母亲往往累得腿疼胳膊酸。
午后,趁龙龙和妞妞睡觉,我母亲洗衣服。洗完两盆衣服,若我父亲在附近的地里干活,她去帮忙一会儿,再回来看看孩子。她把睡醒的他们都抱起来,边扫扫地、喂喂鸡、烧烧水、洗洗菜,边盯着他们不要摔跤。又一晃,太阳落山。我父亲从地里一回来,就要做晚饭了。
晚饭也简单,炒两个家常菜,煮半锅清水面。龙龙和妞妞依然是半自己吃、半要我母亲喂。饭后,我母亲给他们洗澡,或只洗洗脸、洗洗屁股,把他们抱上床。看着他们在床上蹦蹦跳跳,又安静地坐下来看会儿电视,入睡了,我母亲这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。
我母亲另一天的工作,从半夜开始。我父亲一个人在别的屋子睡,夜里,我母亲一个人带龙龙和妞妞,她躺在他们的身边,总是睡不踏实。他们爱蹬被,她要时不时地给他们重新盖好。夜里,抱他们尿尿;他们哭了,她要起来给他们冲奶粉。
在没得孙子孙女前,我母亲做梦也想要一个。老来时,一下子得两个,并且由她来照顾,她显得非常吃力。为孙子孙女,她经常脸色疲倦。在龙龙和妞妞不听话的时候,她更是心烦气躁。她会说,在我和我哥哥小时候,根本没有他们这么调皮。
我心想,我们家是让我母亲最辛苦。我在家的时间看到她太累,便尽力做一些活。我母亲说有我在,她的担子减轻了不少。
有我父亲和龙龙、妞妞,我母亲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空虚。她有一份责任感在身上,这个小世界,已把她的生活装得很满。但我问过她孤不孤独?她说孤独。在她的梦里,也是龙龙和妞妞的哭闹声。
4
我在家,刚好要过国庆节,就给我哥哥打了一个电话,说趁假期该再回来看看了。两天后,我哥哥和嫂子真的动了身。龙龙和妞妞一听说爸爸妈妈要回来,兴冲冲地要我和我母亲带他们大老远去接。等见了面,他们不认识,赶紧扭了脸。跟我回来时差不多,到家后,他们会朝门后面躲,朝爷爷奶奶怀里藏,偷偷地观察这两个人,不愿意多说话。
我哥哥不强迫他们,想抱抱,也躲远远的不看,只留给他们一个背影。我叫不动龙龙,就叫妞妞,让她拿了一个橘子给她爸爸,目的是让他们试着接近自己最需要的人。妞妞居然同意了。她一连拿了两次,第一次缩手缩脚,第二次胆大一些,慢慢地熟悉了,我哥哥趁机会把她抱在怀里。
“龙,妞,来,来妈妈这里!”我嫂子跟我哥哥不一样,她迫不及待地想亲近自己的一双儿女。她那张开的怀抱,就像一个暖意的屋棚,向两个孩子同时发出温情的召唤。只等他们来。她会像大鸟呵护小鸟一样,把他们暖在自己的翅膀下。
龙龙和妞妞不懂妈妈的渴望,惊恐地睁大眼睛,朝后面退,朝一旁躲藏。我嫂子的情绪高涨,只好追赶他们。她就像猫捉老鼠,一下扑东一下扑西,准备把他们逮住。龙龙和妞妞来不及再躲闪,我嫂子很快抓住了每人一只胳膊,他们快被吓坏了,顿时哭叫。好像面前的这个人,不是妈妈,而是一头狼。
我嫂子只能松了手。龙龙和妞妞转身盯着她,一双大眼睛好像在说:她真的是我妈妈?我嫂子笑着说:“我是妈妈,妈妈好想你们的,你们想不想妈妈,来让妈妈抱抱!”龙龙和妞妞同时把头低下来。我嫂子说:“来呀,妈妈不吃你们,喜欢你们呢!”龙龙把脸蒙起来,偷偷地笑;妞妞则不停地眨眼睛,好像在分析别人说的是真是假。
我哥哥劝我嫂子别逼他们,给他们时间来适应。我嫂子噘噘嘴,又朝龙龙和妞妞叫了一句,便无可奈何地住了声。龙龙和妞妞看看自己的爸爸,又看看妈妈,看来看去,不出声。我嫂子把脸扭开一阵,又扭过来,看他们一眼,嘿嘿地笑。
这下,我父亲来到跟前说:“妞妞,你平时在电话里叫爸爸妈妈,叫得怪好。这可是爸爸妈妈回来了,咋不叫了?快叫妈妈、爸爸!”
我母亲也说:“快叫!龙龙也叫!”
我父亲母亲希望一对孙娃子听话。这是他们在家的成绩。妞妞贴着我父亲的腿,仰头看看他的胡子。他微笑的眼神,给她了一种鼓励,她舔了舔小舌头,好像用了很大的力气,嗡声嗡气的一声“妈妈”,才从她的嘴里挤出来。龙龙却跑到我母亲的怀里,叫了一句妈妈。我母亲把他的头拨了一下,让他对准我嫂子叫。龙龙就又叫了一声。虽然声音小,我嫂子听了,忙不迭地答应。
“妈妈!”
“妈妈!”
龙龙和妞妞接着分别又叫了几声,声音越来越大,叫上瘾了似的。我嫂子一直答应。她想抱抱一对儿女的愿望,还没有实现,龙龙和妞妞依然不到她的身边,使她充满期盼。
直到晚饭后,我嫂子才有机会抱龙龙和妞妞。这时,他们已经脱了鞋,上了床,在棉被上滚来滚去,笑着翻跟头。我嫂子站在床前,生怕他们摔下来。她看到妞妞滚到了床边,就慌忙抱住她。妞妞正玩得开心,没有躲避。我嫂子把她掂起来,摇了摇晃了晃。妞妞又到床上玩耍去了,龙龙被她抱在怀里。她一下子笑得很甜美,做妈妈的幸福感全从表情中流露出来。
夜里,龙龙和妞妞并不和我嫂子睡在一起。另一个白天,彼此的距离感还没拉近,龙龙和妞妞还是不要她。可我嫂子只想和孩子多相处一会儿,仿佛害怕时间溜得太快,她和我哥哥又要走,见不着了他们,所以在第二天下午,勉强与我哥哥把龙龙、妞妞抱到大路上,走了很远,很远。夕阳落下去了,他们还没有回家,我去寻找,在路上,我嫂子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,脸上却飞翔着红霞。
又一天早上,起早赶车。我哥哥来到龙龙和妞妞的床前看了一眼,听听他们均匀的呼吸声,站有一分钟,就跟我嫂子上了路。妞妞这天也醒得早,一起床到处找爸爸。我哥哥和嫂子回家的两天,妞妞后来很享受她爸爸的怀抱。她跟她爸爸最亲。她找不见爸爸,也找不见妈妈,就向她奶奶要。我母亲说,爸爸妈妈给你们买糖去了。妞妞相信。龙龙起床后却说,爸爸妈妈下深圳了。他一定是前一天记住了我们大人的谈话。
5
我到底不是一个两三岁的儿童,能够考虑的只是龙龙和妞妞需要什么,却不能代替他们的感受。我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,他们对我算是很熟悉了,并且有了感情。一天,我听到妞妞轻轻地叫了我一声妈妈,我感到吃惊。这孩子大概以为对她好一点的女性,都是妈妈。
生与熟,就是不同。当他们对我感到陌生时,我就是个外人,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排斥;一旦体会到我跟他们的爷爷奶奶一样,可以依赖,也就开始亲近。他们很黏我,我进屋,他们进屋;我上厕所,他们也跟着,成了两只跟屁虫。我常常看着他们,心情复杂。
有时,他们的一个动作,会激发我对自己小时候的回忆。我会想着我和哥哥、甚至更多的山区孩子,长大后走出大山的种种艰辛,而他们不过是我们小时候的重现。惟一不同的是,我小时候可以留在父母身边,而他们却不能够。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留守老人、留守儿童的报道,现在我们家就是。留守,意味着什么?我父亲母亲和龙龙、妞妞正在体验。
龙龙和妞妞长啥样了,长多高了,变没变?我哥哥和嫂子没回来前,想看看他们,我便充当着摄影师,用手机拍照。逢照相,我要选择一个好天气。早上起床,我母亲就给他们每人穿上干净的衣服,然后给他们洗洗脸。等吃了饭,梳梳头,太阳升高了,我便开始行动。我选的背景里,是几间瓦房,或者山峰、一棵树、一片菜园。能够方便选择的,只有这些。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,就让他们蹲下来,要么手拉手站着一起,面朝我。往往这样,他们缺乏耐心,我需要抓紧时间瞄准他们,点击拍摄。其实,他们喜欢前镜头。从前面,他们可以看到自己。他们喜欢看娃娃。里面的娃娃,让他们感到兴奋和新鲜。只是从前镜头不好拍,往往他们看着自己的形象,直朝手机跟前跑,两只小手也同时朝屏幕伸来,嚷着要娃娃从里面跳出来。我一时半会儿拍不成,只能再次调整好位置,点屏幕。若逢下午拍,他们的衣服已经穿脏,入了镜头,就不太美观。这样子,我得多拍些个镜头,挑选几张效果好一点的,发给我哥哥和嫂子。
带龙龙和妞妞到路上的时候,我的镜头里最多的却是草。龙龙和妞妞把到大路上逛逛,已经当作一种生活习惯。哪天不来,就好像少吃一顿饭、少睡一个午觉,总少点啥。我没有恰当的理由阻挠、劝服,就该满足他们这点小小的要求。上路时,一个娃娃趴在我的背上,一个娃娃自己走在前面,我们慢吞吞地摇晃,一分一秒的时间,仿佛被我们牢牢稳稳地踩在脚下。记录一株草,就像记录一个人,碰到某株看着顺眼的草,我便停下来,为它拍照。龙龙和妞妞站在跟前看。我拍好了,换一个娃娃背在肩上接着走,不一会儿,放下来再拍另一种草。走一路,拍一路,草就成了我跟龙龙、妞妞沟通的对象。在青乎乎的草路上,他们也像两朵盛开的小喇叭花。
我确实怀有目的,除了自己对植物感兴趣,也充当老师,教他们认识。我们绕着自家下面的路走一大圈,又走回去,似乎有所收获。但路上的东西,好像跟龙龙和妞妞的关系还不大,他们记不住。他们能记住的,是我们家院子、屋里和他们自己身上的一切。
“龙龙,你的鼻子呢?”我问。
“在这儿。”龙龙伸出一根手指摸摸自己的鼻尖,嘿嘿一笑。
“头在哪儿?腿在哪儿?”我又问。
龙龙便摸摸自己的头,自己的腿,说:“这儿,这儿。”
“耳朵在哪儿?嘴巴在哪儿?手在哪儿?”我继续问。
“这儿,这儿,这儿。”龙龙每回答一个问题,像先前一样相对应地摸摸自己。一一答下来,全部正确。
这些问题,我转而问妞妞。妞妞可以跟她哥哥一样,一一答出。两岁零八个月了,他们已经开始认识自己。这些,他们的爷爷奶奶教过,他们已经牢记。那么,我要另外问问。“哪里是天空?”我看着他们。
两个小不点听了,都咧咧嘴、眨巴眨巴眼,很茫然的样子。原来这个新问题,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我便抱起妞妞,拉上龙龙,来到院子,让他们把头仰起来,看着上面,说:“我们头顶上,那么大的一片,都是天空。”教他们认识天空是必须的,我一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句子。
“天。”龙龙和妞妞同时伸出手臂,指着头顶上面的苍穹。
“嗯。地在哪儿?”我跺跺脚,指着地面说,“这是地。在我们的双脚下面。”
龙龙和妞妞低下头,看着地面,跟着我说:“地。”
龙龙和妞妞学几遍后,我又教他们认识云彩和山峰。他们一次学这么多记不住,过段时间问,他们又忘记了,我还得重新教。我一个星期内教过五次后,再问他们,他们就像了解自己的鼻子和耳朵一样,可以流利地回答。
龙龙和妞妞还喜欢动物。我把买来的挂图贴在墙上,他们每天站在跟前看。半个月后,一张挂图上的二十种动物,他们全部认识。
能够看到他们的进步,我很欣慰。
给我最深的印象是,他们没有好鞋子。
这是我这次回来,刚一进门坐下来,在他们跟进来后看到的。当时,妞妞的脚上,穿的是一双旧了的布鞋。黑色的鞋面上,沾满了灰。她的一只鞋的鞋头,还破了桐籽仁大的一个洞。龙龙穿的是去年的凉鞋。鞋好像小了,显得挤脚。我歇了会儿后,问母亲,母亲声称他们有鞋穿,很多鞋。我把母亲给他们收拾的一个鞋篮找出来,拿到堂屋门口看了看,里面全是几双又旧又破的鞋子。这件事,我记在心里。隔了几天,我去镇上,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新鞋回来。
有时我想,如果不是龙龙和妞妞,我就已经忘记了小孩子喜欢什么。龙龙和妞妞喜欢崭新的东西。在我把鞋拿回来的当天晚上,我让兄妹俩穿上试试大小,他们却远远地看着,不到跟前。我把他们拉到身旁,脱掉脚上的旧鞋,换上新鞋,他们一个个不依不饶,必须把新鞋脱下来,再把旧鞋穿上。仿佛是,脚上的旧鞋再难看,也穿习惯了,穿上很舒服。而新鞋,就跟陌生人一样,跟他们无关,让他们有点害怕,不想招惹。他们这是不想要新鞋?实际上,是我错了。他们只是一时不适应而已。一旦适应,非常欢喜。第二天早上,我母亲给妞妞穿上了新鞋。妞妞自从走出睡房那一刻,总是盯着自己的双脚看。时而,她笑着伸出小舌头,瞄一眼别人,意思好像是给别人看她的新鞋。要是鞋面不小心沾上灰尘,她赶紧蹲下来用手抹一抹。龙龙起床后,也穿上了新鞋。他也喜欢盯着自己的脚看。看一看,他到院子里跑几圈,笑一笑。然后,他弯下腰,把鞋摸一摸。
我以为他们这样,已经把对一件东西的喜爱表现到了极致。然而,晚上却发生了另一件事。这件事,发生在妞妞身上。她不肯脱鞋上床。我母亲给她脱一次鞋,她嚷着再穿上。一次一次脱,一次一次穿,哄不下来,只好让她穿着鞋上床。上床后,我和母亲哄着把她的鞋脱下来,她同意了,但要求把鞋放在她的床前。我们按她的要求做,放在床前的地上。她马上又说她看不见,要放在桌子上。我只好拿起来,放在了床边的一只小桌上。她躺着,翘翘小嘴,忽闪几下眼睛,认真地观赏一番,又提出意见了。这次,她想把鞋拿在手中。把鞋拿在手中睡觉,还是我和我母亲第一次碰见。我母亲说天也不同意,说鞋底脏,这样会把被窝弄脏了。妞妞不行,不给她,看到她哭了,我便想出一个办法:把鞋装进一只小塑料袋,递给她。妞妞马上伸出双手,笑着抱住鞋。然后,她慢慢地进入梦乡。
留守,是一个沉重的词语。我看到这一幕,感觉一颗心被狠狠地击中,无法收拾……
Copyright 2026-2040 广州启航代生网 广州启航代生网